宗璞:长相思
宗璞:长相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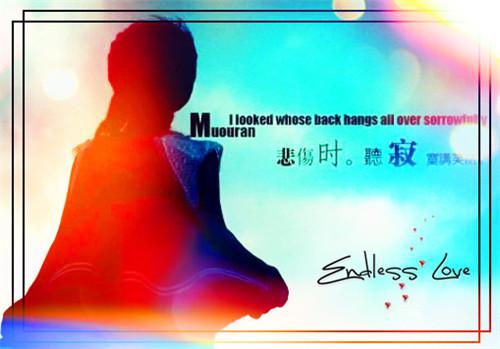
万古春归梦不归
邺城风雨连天草
——温庭筠《达摩支曲》
当我站在秦宓的公寓门口时,心里很高兴。虽然和她不是同学,也非玩伴,交往不多,却觉得颇亲密。因为家里认识,我照她们家大排行称她做八姐。在昆明街角上,曾和她有过几次十分投机的谈话,内容是李商隐和济慈。当时她在上大学,我上中学。这次到美国来,行前她的堂姐秦四知道我的计划中有费城,便要我去看看她。我满口答应说,也正想见她呢,好继续街角上的谈话。“她现在很不一样了,——还没有结婚。”秦四姐欲言又止,“见了就知道了。”
时间过了四十年,还有什么能保持“一样”!
门开了。两人跳着笑了一阵之后,坐定了。我发现时间在她身上留的痕迹并不那么惊心触目,像有些多年不见的熟人那样。她的外貌极平常,几乎没有什么特征可描述,一旦落入人海之中,是很难挑得出来的。这时我倒看出一个特点,她年轻时不显得年轻,年老时也不显怎样衰老。大概人就是有一定的活力存在什么地方,早用了,晚不用,早不用,晚用。
两人说了些杂七杂八的事。她忽然问:“你来看我,是受人之托吧?”
“你堂姐呀,才说过的。”
“不只是四姐。还有别人。”她笑吟吟的,似乎等着什么重要喜讯。
“真没有了呀。”我很抱歉,见她期待的热切神色,恨不得编出一个来。
“你要是等什么人的消息,我回去可以打听。”
秦宓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收去了,呆呆地看着我,足有两分钟。然后就低头交叉了双手,陷入了沉思。我不知道是否该告辞,但是说好晚饭后才来车接我,只好也呆坐着。
她的房间不大,却很宜人,说明主人很关心自己的舒适,也能够劳动。她坐在一扇大窗前,厚厚的墨绿色帷幔形成一个沉重的背景。
“拉开窗帘好吗?”我想让他做点事。她抬头想了一下,起身拉开窗帘。我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片花海,一片奔腾汹涌的花海。这是美国的山茱萸花,高及二楼,把大窗变成了一幅美丽的充满生意的画面。
“真好看!”我跳起身,战到窗前。山茱萸一株接着一株,茂盛的花朵一朵挨着一朵,望不到边。
“这不算什么。”秦宓裁判似地说,“记得昆明的木香花吗?那才真好看!”
木香花!当然记得!白的繁复的花朵,有着类似桂花却较清淡的香气。那时昆明到处是木香花:花的屏障,花的围墙,花的屋顶……“我第一次注意木香花,是和你在一起的。你是我们的证人。”秦宓的眼光有些迷茫。
你们?你们是谁?你和木香花吗?
“那时你是个可爱的小姑娘。他认识你,向你走过来,你说‘这是秦宓秦八姐’。你看见我们在木香花前相识。”
我感觉很荣幸,但实在记不起那值得纪念的场面了。“我没有介绍他吗?”我试探地问。
“他用不着介绍。我知道他,他是你父亲的高足。还会唱歌,抒情男高音,在学校里很有名的。”
我把父亲的高足——我认识的,飞快地想了一遍,还是发现不了哪一位和秦宓有什么关系。不过我已经明白。她等的消息,就是和这位木香花前的高足有关。
“他对我笑了一笑。——一句话也没有说。”她叹了口气,目光有所收拢了,人从木香花的回忆来到山茱萸前。记起了主人的职责。“我们做晚饭吧。端着你的杯子。”她安排我坐在厨房的椅子上,自己动手做饭,拒绝了我助一臂之力的要求。
“你们后来来往多吗?”我禁不住好奇。
“常在校园里遇见,他有时点点头,有时就像没看见似的。你知道吗?”她有些兴奋地说,“有一次新中国剧社到昆明演出话剧《北京人》,我们宿舍有好几张票,我因为要考法文,没有去。后来听说他去了,真后悔,说不定会坐在他身边呢。”她的遗憾还像当年一样新鲜。
“你来美国后他也来了?”
“他先来,我才来的。可我们一直没有见过面。后来他到欧洲去了。后来听说他回去了,消息完全断绝了。”
“你难道不觉得,除了大形势下断绝消息的那些年,他想找你,其实很容易?”
“他一定有很多难处。”她的目光中又是一片迷茫。这目光如同一片云雾散开了,笼罩着她,使她显得有几分神秘。“他一定会来接我。他一定的。我一直等着。”
我不知道说什么好。他们一句话没有交谈过,她却等着,等了四十年!
房角有一把儿童用的旧高椅,和整个房间很不谐调,我走过去看。
她说:“这个么,我帮别人修理,还没有修好。”
“你做木工?”
“无非是希望自己对别人有点用。”
我要帮着摆餐具,她(www.wolizhi.com)微笑道:“呀!你不会摆的。”说着她迅速地摆好餐桌,样样都是三份。
“还有客人么?”我不免问。
“就是他呀。”她仍在微笑。“我觉得他随时会来,如果没有他的座位,多不好。”她一面说着,一面仔细地把一张餐纸叠成一朵花,放在当中位置上。我们两个相对而坐,我们的餐纸都没有用心叠过。
等一个不会来的人,有点像等一个鬼魂。天黑了,窗帘拉上了,遮住了山茱萸。我觉得屋里阴森森的。她可能喜欢这样的气氛,渐渐高兴起来。举起杯子对我表示欢迎。说我的到来是好兆头,证人都来了,本人还不来么?我不便表示异议,只好笑笑,呷一口果汁。她提起昆明街角上的话题,兴致很好。
宗璞作品_宗璞散文 宗璞:废墟的召唤 宗璞:花的话


